新闻周刊丨脱贫之后 乡村振兴是怎样的画面?
|
白岩松: 本周四,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正式更名,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因此挂牌成立。在这个动作的背后,是一个漫长的老故事,当然也注定会是一个新故事的开篇。这个老故事就是脱贫,随着去年年底脱贫攻坚工作圆满结束,近一亿中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,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。一个问题的解决,往往伴随着一个新的目标的诞生,全面推进乡村振兴,就成了新的关键词。在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背后,新的目标将如何去面对和实现?乡村的全面振兴,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? 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,来了!本周四下午,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,更换了新的门牌。这距离我国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,消除绝对贫困,刚刚过去不到几个小时。新的名字,新的起点,更意味着迈向新的使命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: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,表明了我们下一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,全面转向乡村振兴,并且也表明我们乡村振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,需要动员很多力量,各个部门都要参加,这也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,来协调组织相关的工作。之所以对这个局,有这么高的关注,因为涉及到好几亿农民的根本利益。我们国家现在主要差距是农村跟发达国家农村差距,那是相当大的,你要国家要全面现代化,主要的瓶颈就是在农村。
与脱贫攻坚相比,乡村振兴的任务范围,从贫困地区、贫困人口,拓展到了所有农村,全体农民。未来,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职能,也将因此进一步拓展。但现阶段,摆在眼前最为重要的任务,仍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。而这,由原扶贫办整建制转换而来的队伍衔接,自然也就更为顺畅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:我们乡村振兴,某种程度上就是照搬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,比如说我们中央统筹,省负总责,市县落实,这是脱贫攻坚提出来的,乡村振兴现在也是这样的工作机制,那么五级书记一起抓,这也是脱贫攻坚提出来的,乡村振兴也是一样的。未来也有东西协作的问题,驻村工作队,第一书记可能也需要类似的队伍,那么在具体的政策方面,也有很多延续性。
为了推动“三农”工作的重点,从脱贫攻坚平稳地向乡村振兴衔接,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对摆脱贫困的县,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。期间,不摘责任、不摘政策、不摘帮扶、不摘监管,帮扶力量保持总体稳定。“冲锋式”的脱贫攻坚,解决的是“不愁吃、不愁穿”等基本需求。而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,就要以持续增收为落脚点,使农民自身具备向上提升的能力。保持农村的产业振兴,成了至关重要的课题。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:产业发展是个持续过程,不像危房改造,把房子给你修好了,多年不用管了,那产业可不是这样。你必须要不断去提高他的技术水平,适当扩大规模,培养新型经营主体,这样才能够稳定增收,或持续脱贫,这些方面,需要持续的扶持政策。你不能说有些贫困户,自己搞产业,能力不够,可能通过能人大户,正在带的过程中间,突然脱贫攻坚完了,我不管你了,这样可能就会出现问题。
四年前,通过上海企业的对口帮扶,贵州省望谟县洛郎村,原本广种薄收的板栗,成为某航空公司的固定餐食。凭借这笔收入,洛郎村当年就实现了贫困村出列。但宣告脱贫后,当地没有停止相关政策的帮扶。相反,为将板栗真正发展成产业,他们持续追加了近1000万扶贫资金,修路、铺设灌溉设施;同时,省里下派农技人员,将近7000亩低产板栗林,进行了改造。 如今,相关的扶持政策仍在持续,该村也已发展成为种植面积达1.7万亩的,板栗高产示范园。他们的板栗,凭借出众的质量,闯出了自己的品牌,除了供应飞机,更畅销全国。当地还在板栗林下,追加引进了林下养蜂、林下养鸡等产业,特别是林下栽培食用菌,更让参与的村民,额外掌握了一门技术,追加了一份收入。
贵州省望谟县平洞街道办洛郎村村民 岑洪发:以前没有发展食用菌,我们就出去浙江打工。现在这两年,我们洛朗发展了,我直接在家里面做事,这个工资也是高的,普遍工资3000多,还要加上一年板栗收入8000至10000左右,现在我就不出去打工了,在家里面得照顾老人,得照顾小孩。 据统计,发展板栗产业前,洛郎村的有效劳动力中,有912人外出,到江浙、广东等地打工;如今,通过板栗等产业带动,全村产生了致富带头人50余位。看到钱包渐渐鼓了起来,近400人选择不再外出,就近在产业园工作。人留下来,空心村慢慢恢复成实心村,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气,也一点点充实了起来。
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:我们现在回去很多,也不是回到村里去了,有些回去,回到县城,回到镇上面,工业区里面就业,是这样一个过程。未来乡村振兴跟新型城镇化,同步推进,协调发展,县城今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,多数县城会形成几十万的规模。有专家预测到,到2050年,全面现代化的时候,80%的人都生活在城镇里面,以农业为生的,人口10%都不到。全面现代化基本的特点,城市和农村没有根本性生活质量差距,收入应该是差不多的,公共服务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,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。农村不可能搞得城市那么热闹,农村更加宜居,更加生态,更加自然,田园风光,所以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。 白岩松: 去年年底,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,这可不意味着从此人们都过上了不再贫困的生活,这属于童话的结尾,但不属于现实。因病返贫、自然灾害导致的贫穷挑战等,依然会不时地来串扰。因此,未来“十四五”的这五年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,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。对摆脱贫困的县来说,这五年是过渡期,要做到扶上马送一程。这五年的时间看着长,但其实依然很有挑战性,因为从脱贫到振兴,有太多的工作要做。比如说:农民想要生活更好一些,有的就需要金融的扶持,但银行往往不愿意给小农户发放贷款,未来这个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吗? 谁给农民贷款? 柴永峰生于曾是国家深度贫困与脱贫攻坚重点解决地三区三州,是我们跟拍将近三年的扶贫工作者,就职于属地监管下的小额信贷公司。他不找等、靠、要的人,迈开腿扫街,找那些想通过小额贷款撬动美好生活的贫困群众。
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:轻易的、白给的东西,它的作用不大,就跟我们吃苦的人一样,你没有吃过苦,你就不知道甜的滋味。我们的贷款也是这样,给你贷了,还得不多,但是你每天把老百姓(603883,股吧)的惰性给改变过来,第三个月就开始还钱了,时间比较急,一天都不能拖,必须按时按点还,要讲信誉。
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:农村金融当中普遍问题,主要就是说农民缺少抵押物,那么银行的不能提供贷款,那么信用贷款就是不需要抵押物,它就凭着农户的信誉就放贷款。但是农户的信用是哪来?有行为轨迹的可以在线上收集,没有线上轨迹的可以在线下收集,传统的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,去在农村走村串户收集信息,就是为了建立这个农户的这个信用评价体系。
孙同全长期研究扶贫中的小额信贷问题,他所在单位于本周四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。他注意到,柴永峰现在所在机构70%左右的客户,因无抵押无担保更无征信,依然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。他认为,此次一号文件强调,用3年基本建成较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,切中群众获取金融服务痛点,正需要像柴永峰这样的人。贫困程度越深,柴永峰贷款越谨慎,放贷前要做家访、进行第三方询查,即便是老同学,若无实体规划绝不放贷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:信贷当中掌握的技术要求有三个C。第一个是这个Capacity,就是能力,他们家的金融状况,他们家的经济实力;第二个是叫Character,就是人的品性,是不是讲信用,为人怎么样;第三个C是叫Collector,就是担保物,现在因为农民没有担保物,所以第三个C是非常弱的。信用贷款更注重的是第二个C,是人的品性,品质是否讲信用。
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:每个人都有贪心,假如说你现在人家给你抽烟,下次贷款的时候,不是额度也提高了吗?我说我们贷款不是为这两盒烟来,我们贷款就是让你发展。 孙同全注意到,按最高法规定,目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.4%,柴永峰所在机构也严格按照该利率放贷,实际上,作为属地监管机构,它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,可根据人吃马喂等成本实际,决定自己的利率线,保持微利。 通过实体物质推断经济能力,熟人社会搜集品性等软信息,对农户信用进行画像,识别出迫切想改变命运的人,进行放贷。柴永峰总是说,大多数客户淳朴可信,但这种品性更需要后续维护。放完款,才刚刚是他扶贫路上第一步。他要按规回访,调查客户是否把钱用在实处而非滥用,还会告知一些经验改善经营。若到了还款期还未到账,他又得跑去催逾期,频繁见面沟通给客户带来正向的催款压力。
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:有的时候它不是做慈善,贷款不是在人情的圈子里面跑的。我们如果贷款了以后,我们信贷员就成了一个管理者了,每一个客户都需要你去考虑,都需要你去监督,都需要你去催促,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,得想别的办法。 这些年柴永峰跟我们诉了不少苦,更多挑战来自平台数字化更新,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的要求,他不仅要自己学会,还要赶在逾期影响客户征信前,开车去教客户快速还款,每个客户常常来回教几次。 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:我跟他就说了,转账的时候,就跟那水管里的水一样,从我这边输到你那边去,那边堵住了以后,钱退回来了,不会没的,你放心点的就行,没事。他就慢慢敢拿起手机点了,不然不敢点。
事实上,即便能从传统银行贷款,但因脱贫对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极度敏感,让人倾向投靠亲戚朋友的私人贷款。在我们拍摄期间,孙同全做了一个统计,中国农村的私人借贷,占整个农村借贷总量的60%左右。这让他更加坚定推广小额信贷的决心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:致贫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,整个资金缺乏往往是最大的一块短板。中国现在大机构是不缺的,最缺的就是能够为这些小微的,这个信贷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。我们一直也在呼吁政府,就是给这样的一些机构,能够解决这样一个法律地位上的问题,明确一个合法的地位,让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放手去干。 天祝县去年二月份脱贫摘帽,一号文件强调,像这样曾经的深度贫困区,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,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,防止规模性返贫。小额信贷以及已实施的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押贷款等业务,将在今后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。但放眼全国,虽然天祝脱贫了,其与发达地区仍存巨大鸿沟,还需要金融扶贫之外的更多支援。
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扶贫办原副主任 赵生成:比如说资金的问题,技术的问题,产业发展的问题,还有教育、医疗、卫生、住房这些问题,一方面需要政府推动,一方面也需要社会上的技术人才力量的支持。 接触柴永峰的时间大多在车上,他常常来回几百公里,从早跑到晚。但看到客户完成信用毕业、借到款、生活步入正轨,所有的苦都成了幸福。脱贫摘帽后的乡村振兴,他选择初心不改,奋斗在路上。 白岩松: 从现在看,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地解决,但请注意,强调的是绝对贫困。但是相对的贫困,在未来依然会存在,更何况水涨船高,人们对美好生活总会有更高的期待。而另一方面,脱贫攻坚从某种角度来说,是硬扶贫问题的解决,而软扶贫依然在路上,这个软就包括着文化,教育,智力等等很多层面,在这些方面,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依然是贫困的。比如中国90%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初中以下学历,其中小学文化、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超过50%,远高于平均水平,接下来我们该继续做些什么? 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出来 这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对于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一次调研,七星关区已于2020年3月退出贫困县序列,脱贫近一年后,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,是本次调研的重点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我去过胡家贵那个家多次,他是属于那种扶贫的重点,能力相对差,这个又不肯去努力。国家已经载帮了他很多了,很早就帮他修了房子,然后又帮助他这个生产方面,种植、养羊、养猪都不太成功,最后给他一个护林员的工作。
43岁的胡家贵只有小学文化,在他家的墙上,保留着他当年用最简单的计数方式写下的打工工资,这些数字,记录着这个家庭曾经的贫穷。如今,护林员的工作让胡家贵家生活有了基本保障,但卢迈更关心孩子受教育的情况。胡家贵的妻子有智力缺陷,但是两人养育的子女却多得惊人。几年里,卢迈四次来访,每次这个家庭都会增加一个孩子,而这次也不例外。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第六个了,问他为什么,我从四个的时候我就问还生不生,不生了,结果还接着生,最后说实话,他们在村里头是单独的,他们是从外边过来的,怕受欺负,所以希望多点孩子,这个在毕节可能特别普遍,因为他们处在(三省)交界处,这个村落的形成,人口的结构,就是这么一个格局。家里头因为奶奶也岁数大了,爸爸妈妈对孩子也缺少照顾。他的大女儿,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她已经上小学了,以前看过她做作业,那会儿她五年级,都是中国字,但是一句话都念不懂。 在卢迈和同事们扶助过的贫困家庭里,像这样缺少家庭教育和照料的孩子,还不在少数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这个家庭就是也是很值得让人同情的,两个儿子,一个儿子去世了,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头打工,这两个儿子有4个孙子。妈妈都是走了,所以一个70岁的老太太带着4个孩子,我们说那个孩子去医院,7岁的他现在在幼儿园,是那个5岁半的孩子在带着他,干什么事就他的兄弟,堂兄弟带着他,照顾他。
毕节七星关区,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,也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。贫困带来的其它社会问题也较为复杂,使得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,一出生就深陷教育的荒漠之中。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单亲、留守、贫困、家暴和我们说的残疾,我们整个就刚才说的五个因素,有一项的,在贫困地区调查中,大概占60%,超过60%。那么这样的家庭里头,孩子他成长的时候,孩子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,要注意家庭是什么情况,而且对外来的任何人都会害怕,都会怕生,而且营养不够,没有互动,所以对他的很多功能,语言功能什么的都发育不好。 在脱贫攻坚之战中,各地对于教育脱贫的投入主要在义务教育阶段,而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相对较弱。但在卢迈看来,贫困家庭原本在家庭教育上就比较薄弱,一些村庄又没有幼儿园导致儿童无法进行学前教育,这使得一些孩子进入小学后也容易面临困境。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我们对控辍保学,是花了很多精力的,也很重要,让所有人都能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,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。但是他的根源是什么?为什么他们在学校里头他学习不好,厌学然后辍学了,最重要的还是他没有做好早期的入学准备,不会普通话,然后上来一二三年级的那些东西听不懂。一步赶不上,步步赶不上,越学越困难,那他就辍学了,你要是真的预防为主把学前教育办好,不要让他上学的时候就跟不上。
五年时间里,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当地政府的努力下,七星关区偏远农村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,而针对0~3岁贫困孩子的养育问题,他们发起的“山村入户早教计划”共培训育婴辅导员75名,每周一次,为855名困难儿童的家庭提供早期养育指导。但这些努力,对于教育这项长期的事业来说,还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。
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:我们现在可以靠救济,他们是低保,国家也有救济,给他一个公益岗位,像护林员,像这个打扫卫生也能够满足他每个月最低有个800元、1000元的收入,这样能够摆脱绝对贫困。另外一个在收入支持外就是能力建设,治贫先治愚,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,通过教育培养能力,使这个孩子能够成长起来,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挣到收入,这才是根本之策。
白岩松: 一个个体、一个国家向前走,总是需要有目标的,而一个目标完成了,就总需要有新的目标,让人们知道往哪儿走。对于中国来说,小康任务完成了,接下来就要奔向2035和2050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。而面对乡村,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了,接下来就是乡村的全面振兴。因此,此时又是一条新的起跑线,保持冷静,继续前行,只要持续地走,目标就会越来越近。 视频制作丨姚道磊 张大鹏 徐 新 微信编辑丨马诣宸 (编辑 汤嘉铭) |




















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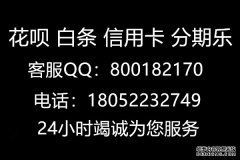





评论列表